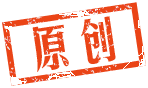|
额尔登布
(一)
皇城根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戏园子里、茶馆里、大街上,衮服短褐有闲有忙,或吐着烟枪高谈阔论,或蹲坐在路边袖着手看人就地下棋,或奔波在那熟悉的几条街挣够那几文子儿能泡上壶茶歇歇脚。天边几片安逸的云彩偶尔被路过的某位侍郎的官轿冲击一下。
额尔登布从佐领1家出来,一身素色的袍子罩一件棉坎肩,背着手,皱着眉头慢慢向家里踱步,这年关将近。多少年钱粮还是一成不变的这么一点儿,自己的那点俸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就这上边还发不下来。祖上留下的那些地产,老太爷年轻时候就给偷偷卖了。想自己倒腾点买卖什么的吧,律上明摆着不许干,阿玛2也不许自己去干这丢脸的事儿。可总不能就一直这样坐吃山空吧。 想着想着额尔登布就和一人迎面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发小、副前锋校3双宝,俩人互相打个千儿。双宝笼着手,“我说额大少爷您出来怎么不喊顶轿子啊,您瞧这天阴的,怕是雪没几个时辰就下来了。”“哎呦,这不是想事儿呢嘛,”额尔登布拱拱手,“双大人您这是有何公干呐?”双宝拉着额尔登布边往墙根走边跺脚,“嗐,我能有什么公干!您别价,您可别喊我大人,您可是世职在身上的人呐,哎,今晚儿咱去烤肉宛来几盅?” 额尔登布嘟了两下嘴,“不成不成,大爷我这几天手头紧着呢。”“哟。您跟我谈这个干嘛?咱爷们有银子。走走,家去换身鲜亮衣裳,别跟爷这显摆你额大少爷有多寒酸!”双宝搂着额尔登布的肩,一起出了胡同。
额尔登布,整蓝旗下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官儿,姓乌拉那拉,今年刚满十九,一般个儿一般人儿,前额总是刮得青青的,一条辫子也总是梳的干干净净。白净面皮上一双忧郁的眼睛,一根直挺的鼻梁,一张总是欲言又止的嘴。祖上曾挣过一等轻车都尉兼一等云骑尉4的世职,虽然一直袭着,可是一大家子向来花费甚糜,到了额尔登布长大了,祖父也丢了在内务府的差使,一家子男人只能闲的到处溜达。倒是额尔登布做了个笔贴式5,每天做些抄抄写写的小活儿。 雪花儿又飘了起来。今年的雪可真是多,额尔登布不停搓着手,一面走进自己家那间老宅子,阿玛大概又和内帮叔叔大爷们摆弄八角鼓去了,额莫6兴许是在隔壁同几位大姑奶奶玩牌呢,总之家里没人,双宝又先家去了。 拍完身上的雪,额尔登布正要进屋里烤烤火,便听见有人推门而入。看看天井里是熙兰领着他二弟观音保进来了。观音保蹦跳着给大哥打了个千儿就冲进屋里找炭盆。额尔登布便笑着把熙兰让进屋里。熙兰是隔壁家的小女儿,今年十七了,和额尔登布打小儿一起长大的,是个胡同里出了名的稀罕人儿。 额尔登布看弟弟往里屋去了,就一把挽住了熙兰,熙兰反过来抱住了他,笑吟吟地互相看了会,熙兰又红了脸轻轻推额尔登布,“快放开我,观音保出来看见多不好。”“没事,这小子肯定抱着炭盆亲呢。”额尔登布给她额头印上一个暖暖的吻才恋恋不舍的放开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抚着她的小脸蛋儿,“今儿晚上和老双几个去烤肉宛,回来路上给你带桂花糖蒸的栗粉糕。”熙兰撅起嘴巴,“不要不要,总拿些甜饽饽来贿赂我。”额尔登布翘起眉毛,“是吗。那爷就不给你带了,爷那还有个相好,要不爷给她带,哈哈。”熙兰娥眉一皱,转眼间换了一副可爱的怒相,拍打起额尔登布来。 世界莫过于此了吧,额尔登布攥住爱人的小手儿,默默想到。 “前方大捷了!!阿桂7将军大捷了!!!” 一路黄尘,一名戈什哈(侍从护卫)去向紫禁城方向,两边的百姓纷纷退让,一片狼藉。双宝不顾身上扑满的尘土,张着嘴呆呆的望着戈什哈的背影。“你看什么看啊?”额尔登布给他一掌,双宝回过神来,摇摇头,“可惜爷没去。”额尔登布一脸鄙视,”走吧走吧,您这位副前锋校大人一年上马次数还没爷多呢,还打仗呢您。”双宝怒视额尔登布,“这年头咱们旗人有几个能打仗的!可是要是我们营去,三爷我肯定给挣出个巴图鲁8!” 额尔登布甩甩胳膊,“走吧走吧,先看看你身上银子够不,爷跟你出来就不用带银子了,赶紧去叫顶轿子过来啊。”
(二)
这个年总算过了,纵然艰难了也仍然过的像模像样。一直到开春暖和。 没想成今年碰上了选秀女,额尔登布在衙门里咬着笔杆子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心头一紧,冷汗涔涔地流下来。按规矩,熙兰是无论如何也得参选的。额尔登布摘了暖帽擦一把汗,一面安慰着自己,那么多旗人家女儿,怎么就会一定选上熙兰呢。可是转念一想,熙兰的容貌,除非眼瞎了,谁不会喜爱呢。又盘算着是不是该使上点银子给佐领大人叫他不要给报上去,脑子里又冒出熙兰的阿玛得知女儿可以参选秀女笑哈哈的样子。一面又悔恨自己不敢早早地给熙兰家提亲。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直到天色暗下去了众人都一窝蜂的回家时候才慢慢冷静下来。 连家都没回,额尔登布便借去找熙兰的哥哥长顺的名义去她家瞅瞅,熙兰看见额尔登布还戴着素金顶子9就匆匆忙忙地来她家,大方地把额尔登布迎进堂屋,她阿玛赫四爷在,额尔登布给磕了个头就坐下了。话没说上几句,赫四爷就扯到选秀女的事情,额尔登布看到赫四爷那笑逐颜开的表情。就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主,人家眼睛里的全是上面的。 出来的时候额尔登布把熙兰拽到一遍,心急火燎地问,“你就不能和你阿玛说说你不想去吗。”熙兰眼泪扑簌簌地就掉下来什么话也不肯说,反而转身抹着眼泪回去了。 额尔登布狠狠叹一口气,低着头出了赫家。 熙兰的表情与态度让他心生恐惧。 回家给祖父、额莫请完安,连饭也不吃就回厢房喝闷酒,额穆叫房里的丫头瑞儿端来些饭菜放那一口都没动。反而丫头叫浑身是火的额尔登布一把按在床上,可怜的小丫头连叫都不敢叫,眼泪就下来了。额尔登布刚要动手,就停下来皱眉给瑞儿擦了一把眼泪。把瘦小的她拎了起来,挥挥手,“走吧。” 阿玛拎着鸟笼子不知道打哪儿回来了,听说额尔登布饭也不吃就回屋大发脾气,站在天井大骂起他,额尔登布出去给阿玛磕了个头就一言不发地回厢房了,倒是老爷子拄个拐杖把阿玛拎回去了。堂屋就传出来老爷子的怒骂。 额尔登布约摸喝了二斤酒,后半夜便倒头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未时左右,揉揉睡眼,便看见丫头瑞儿怯生生地候在一边,说道隔壁赫家格格10一直在等着少爷呢。额尔登布按按自己还有些痛的额头。起身出去。 熙兰坐在额尔登布的书房,仍然是落落大方,额尔登布愣在那儿,盯着熙兰额前细细的发丝。忽然觉得她一定要是我的,不管是谁抢都不行。 “四十八儿11。”熙兰站了起来,“我不愿意去选秀女,即便我阿玛和额莫要我去,我都应了一定要嫁给你的。”额尔登布神色似是癫狂下的宁静,微笑着听着爱人的话。熙兰仍然稳重大方不紧不慢的说,“放心。我阿玛和参领12大人素来交情好。他老人家怎么会把我往火坑里推呢。” 额尔登布脑子里慢慢转着,赫四爷的女儿要是选了进去。怕是赫四爷就不是现在一个毫无用处的副参领了。他不是一直想寻个油水差事做么。熙兰见额尔登布半天不说话,轻轻嗔怪似的戳了他一下,额尔登布反而笑眯眯地说,“小心肝儿,你放心嫁给我,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贴式。” 熙兰细弱的鼻翼难以察觉的抽动了一下,整个身子慢慢陷在额尔登布满是酒气的胸前。
(三)
额尔登布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四九城几乎被跑了个遍。甚至是从没去过的宫城。本牛录13的福老叔在西华门当差,额尔登布在差房喝了杯茶。虽然门外是荒凉了些,也一样能看见巍峨不可攀的宫室。额尔登布倒吸一口凉气。这里面住的,不就是祖宗们用几代鲜血给捧上去的吗。 一想到熙兰,心骤紧。一种身体分作两半的感觉贯彻全身。 怀揣着几张簇新的银票,额尔登布踏进佐领塔山家里。塔大人是本牛录佐领,年纪不大,刚过三十,一脸精明。额尔登布给塔山磕了个头。就分宾主坐了,“额老弟,听说兵部评定,要给您评个一等笔贴式?”额尔登布欠欠身,“这个倒都是传闻,塔大人您是别信。就老弟这小年纪,怎么可能。”几句闲磕过去,额尔登布略略按了按发麻的太阳穴收收心,笼着手把那几张银票塞进塔山的袖里,小心翼翼地问塔山,“老哥,这不过几天选秀女么?您看看帮老弟点儿忙如何?”塔山把银票往里掖掖,睁大眼睛,疑惑地回道,“嗯?这个倒是老哥我的事儿,可是你们老乌拉家可近年儿也没有该着选的吧?” 额尔登布轻轻咳了声,“不是不是。家里的事情自有老人们操心,哪里轮得到我。”说完向塔山探探身,“老哥,知道赫四爷家的小女儿吧!” 塔山点点头,“知道啊,那可真是个可人儿。赫四爷可有福气了,这一选上去,保不齐这丫头就伺候万岁了。”额尔登布脸一沉,“老哥您误会了,”“此话怎讲?”塔山饶有兴趣地拈着胡子,“您瞧见了,咱也打开天窗说亮话,熙兰,赫四爷家的小女儿,老弟我稀罕她,所以咱来求着老哥您帮衬着点儿,您只要一句话,熙兰就给免下来了。” 塔山眼珠晃了两下,沉吟着掂量一下银票的厚度,估计有个四五百两?不用多会儿功夫,塔山便笑道,“这个便是不太容易,既然老弟求老哥了,咱就尽着点儿绵力,给您压压。 额尔登布赶忙起身伏在青石板砖地上给塔山重重地磕了几个头,“全都仰仗老哥您了!”
额尔登布都快乐得笑出声来了,满面春风地同诸位同僚见礼,几位稍年长的笔贴式疑惑地看着近几日总是郁郁寡欢的这位小弟突然又变的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连鸟笼子都顺带遛到差房了,总之这种情绪也感染了诸位大人们,话题从某省制台府里的戏子一直扯到萨六麻子新购的海东青14。甚至连那连篇累牍的公文也成了众人相互掐趣的对象。 天儿一天天暖了起来,换上新做的湖绸褂子,额尔登布觉得神清气爽。恰在这时司里遣了额尔登布一人去南京交接些公事,而选秀女的大日子也渐渐近了。 熙兰从额尔登布家后院悄悄的进来。老爷子约了双宝家老大人看戏去了。额尔登布就把熙兰领进后院一间库房。库房里一柄连鞘都锈掉了的刀架在当中。额尔登布指了指,“这把刀,是看着咱们俩长大的。”熙兰给刀轻轻蹲了个万福,额尔登布略带惊愕地笑着把熙兰拉了起来,“兰儿,你这是干什么?”熙兰转身已是满眼泪花,额尔登布把她揽在怀里,“你怎么了?我的好兰儿。你哭什么呢?”熙兰仰起头来给额尔登布一个笑容,“没事,等你从江南回来了,我就嫁给你。”额尔登布激动的捧着熙兰诱人的小脸儿,一遍一遍吻着她不断外溢的泪水。 “你是第一次出远门,一路注意着点儿,看好你那点银子衣服和马,到了南边儿也要有个旗下大爷的样子,夜晚须是要防着寒气,住店时候记得上好门闩,把你们家三叔的那把刀系在马上...” 熙兰在额尔登布的脑中调皮的笑了整整两个月。每个异乡的夜晚额尔登布辗转反侧,一面呵着气儿裹紧薄薄的被子抵御南方春寒的阴冷,一面算计着哪天可以回家,可以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盘算着婚礼的筹备。还在夫子庙前的庙会上买了许多有趣的小玩意儿,心里琢磨着兰儿一定没见过。到时候可以看着她露出两颗小虎牙一脸新奇的模样儿。 咱们暂且让额尔登布来回奔波于江南的诸衙门间,回头看看四九城新近又出了什么新鲜事儿。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自然推不动大磨,临了选秀的大日子塔山便一直在心里暗自忖度,把熙兰选了出去,自己自然是首推一指的功劳,若是熙兰选作了嫔妃,或者哪一位王爷选了去,或有些长久的倚仗亦未可知。两下了一对比,塔山不仅犯难起来,又一盘算,额尔登布不过是低等的笔贴式,就算是将来官做大了,以他家现在的地位,亦不过是做到四品京官罢了,又想到家里说过自己太爷当年是和额尔登布的太爷云南打仗时候因兵饷怄过气的,可也当算是报了家仇了吧,遂下了决心把熙兰誊在名册上递了上去。
(四)
额尔登布睡在运河边的一座驿站里,浑身肉说不出的酸痛,虽然天气已转暖,驿馆里还是潮湿寒冷的,免不得烧起炭盆取暖,闻着带着霉味儿的棉被,额尔登布皱着眉头怎么也睡不着。心总是在嗓子眼儿提着,两个多月没有丝毫放下。
远远地总算望见了京城的城墙,额尔登布的心似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他整整风尘仆仆的行袍,又嘱咐身边奴才大方谨慎点儿,故作镇定地进了城内。 先去部里交了差事,额尔登布便迫不及待地往家赶,路过红厂胡同便望见远远的红红的一片热闹,似是哪位王公贝勒15娶了亲吧,额尔登布一直走近了崇文门里才撞上娶亲的队伍,真有气势,竟是隔三岔五地往路边看热闹的散大把的钱,额尔登布来不及躲闪,一枚乾隆大钱儿正中脸颊,眼睁睁看着一队队的人马过去了,便拨了马头依旧往家去。 额尔登布眼看着一直到家里的路上都红扑扑一片,心里不禁起了一股子凉意,冷汗愈冒愈多,果然到了熙兰家门口,看见阿玛穿着簇新的袍子同满面红光赫四爷打千儿作别。 额尔登布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差奴才福三儿去问怎么一回事儿,福三儿去了少时便踉跄着回来磕头,“少爷,是赫家的千金选了做五贝勒夫人了。”额尔登布眼里一阵青黑,一股痰气蓦地涌了上来,登时便从马上掉了地上昏迷不醒。 隔了半日,额尔登布醒了过来,躺在自家的炕上,好似是从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儿,回转过来,目光游移无神,连胳膊也使不动力气似长在了别人身上一般。瑞儿在一旁打了一铜盆热水洗毛巾,额尔登布歪着头看得直心酸。 “瑞儿,过来。”额尔登布勉强睁着眼睛说话,瑞儿一回头,“呀,四爷您醒了。”便端了手巾过来伺候,额尔登布抓着她的手,嘴里不免叹着气,“要我说就别再找什么大家子的女人了,你也别当我的丫头,干脆你现在做了夫人得了。”瑞儿被他拽着手,又不敢脱身,满脸绯红,及至想起自己身世卑微,也只当额尔登布是一句顽话罢了。又听见额尔登布要酒,奈何不得,便斟了一小盏酒给他吃。岂料他反而起身自顾自地去柜里拿了一壶出来,坐在桌边忽哭忽笑地喝将起来。 额尔登布只觉得浑身乏力,一股抑郁之气阻塞在胸口,悲恸不已,或痛不欲生,或释然成佛,而心里又明镜儿似的明白究竟怎么一回子事了,好在还有酒兄弟陪着,喝了个半醉时候双宝和几个发小儿拎着酒坛子来看他。后面奴才们还拎着几个食盒。 额尔登布醉的没法儿打千儿了,站了起来又坐在了地上,双宝把他拎起来按在凳子上,“来,好安达16,我知道你心里苦,什么苦我们兄弟几个是一处长大的都知道,素来的情分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你就是和我们喝酒,别的什么都不要说了。”额尔登布苦笑着点了点头,两行清泪滚滚地烫了一脸。 一场酒直喝了一整夜,到卯时分额尔登布终于又停了胡话浑浑睡去,双宝等人自收拾了冷盘杯盏家去。
且在家休息了三日,额尔登布便去没事儿人似的去了部里。依旧兢兢业业办着属于自己的差事。
约莫过了两个月有余,天气更热了起来,街上做各种生意的人也愈加多了起来,额尔登布趁了闲来无事,约了几位小爷换了凉快轻便衣裳到街上走走,正饶有兴致地赏玩儿,忽有一婢女拽住了他袖子,问了声是额尔登布额大人吗,额尔登布疑惑地点点头,婢女低声请他过去,说有人想见他。额尔登布略一思索,料不能有什么不好的事,于是嘱咐了几人自去逛着便随了婢女往街边一座酒楼去了。 及至上了二楼一座素雅齐整的包间,额尔登布掀开帘子搓搓手,就看见了一位略施脂粉着装简单的贵妇,定睛一看,额尔登布心一沉,故作轻松文雅地磕了个头,“兵部职方司笔贴式,正蓝旗塔山佐领下人额尔登布给贝勒夫人请安。” 熙兰嗯了一声,“起身吧。额大人请坐。” “谢贝勒夫人。” 额尔登布起身,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 “敢问贝勒夫人召奴才有事吗?” “呵呵,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不过是许久没见了请你叙叙旧罢了。”熙兰的脸在额尔登布眼里变得既熟悉又陌生,本来第一眼看到她时的悸动竟然被她眼中折射的冰冷的光芒所冲击地丝毫不剩。再看时她仍然笑靥如花,手里把玩儿着西洋进贡的小怀表,一副慵懒而骄傲的神情。 “岂敢,奴才怎么敢与夫人叙什么旧呢,折杀奴才了。”额尔登布微微笑着。 “是吗?那我怎么听说,我出嫁那天你去我们家闹了个气昏在地呢?”熙兰抬起眼来端视着额尔登布。额尔登布看了一眼熙兰眸子深处,起身作揖,“想是夫人听了不知哪儿来的话猜忌了,奴才那日并不知道是夫人您出嫁,只是长途跋涉未曾休息,临近家门不免受不起舟车劳顿,遂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及至知道乃是夫人您的大喜事,尚悔恨不及呢,怎敢叨扰夫人娘家。” “呵呵,是吗。”熙兰呷了一口茶,“既然如此,念在你父亲素来与我父亲交好,我也不追究于你了。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我在贝勒府里过的很是受用,你不要再外面胡言乱语,惹的我知道了心烦,我若烦了少不得拿你问罪。” “岂敢岂敢,贝勒夫人多虑了,奴才并不敢胡言乱语什么,您尽管放心。我今日未见过夫人,也从未识得过夫人。”额尔登布一揖到地,便听了熙兰咯咯笑了走将出去。 额尔登布直起身来,闭上眼睛长吁一口气。 人毕竟总是会为生活所迫的。 额尔登布出了门,摘了大帽子,摸了一把青青光光的额头上的汗。抬抬眼望望蓝的如一汪湖水似的天儿。然后一步一摇地走在尘土飞扬的街上,时不时轻轻拍打着腿边沾上的灰尘。 似乎是什么都没了吧。双宝的酒没了香味儿,萨六的苍鹰反了性儿,阿玛的胡琴儿弦断了,仓房里太老爷的弓一拉便折了,自己的心空荡荡的不在那儿不知道飘向了哪里。 额尔登布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喜欢和会拉胡琴的,坐在花香四溢的山上,看着远远的健锐营17的营房,一曲终了又一曲,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天黑了才寻到山下双宝的营房凑合一宿。
(五) 也不知道贝勒爷是怎么知道夫人见了一个叫额尔登布的笔贴式,下人们纷纷传说夫人挨了贝勒爷一顿打,在房里气得哭了一天不吃不喝。次日,兵部的堂官被贝勒爷请来听了一出戏后,额尔登布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介闲散旗丁。
双宝新近晋了前锋校,娶了一房媳妇。
“准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和珅等奏,送原兵部笔贴式额尔登布到部转发拉林种地一案内,称臣旗参领云升等详据佐领塔山呈称,职佐领下原兵部笔贴式额尔登布素行凶顽,不守本分,屡误差事,贻误军机,并多次醉酒后斗殴生事,不服拘管,似此不法之徒,未便容隐,相应照例,呈请发遣等语。该职等查得。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内八旗王大臣等议。”
那木图
一零年八月十六 注释:
1 佐领:清代八旗官名 2 阿玛:满语,意为父亲 3 副前锋校:清代八旗武职 4 一等轻车都尉兼一等云骑尉:清代封爵 5 笔帖式:清代低等文职官名 6 额莫:满语,意为母亲 7 阿桂:乾隆年间满族著名将领 8 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清代常作为封号使用 9 素金顶子:清代七品官员所戴之顶子 10 格格:满语,意为小姐,姑娘 11 四十八:主角小名 12 参领:清代八旗官名,系佐领上级 13 牛录:满语,为八旗的基本组成单位,主官即佐领 14 海东青:满族人善于驯养的一种名贵的鹰。 15 贝勒:清代宗室封爵 16 安达:满语,好朋友之意 17 健锐营:北京西郊的八旗驻防部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