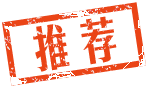|
一位俄国翻译的满语情结 文、图/潘小松 多年前笔者偶得一本《满俄大辞典》,束之高阁许久。近读阎国栋先生著《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才知道它是很了不起的双语辞典。 俄国翻译在北京 此书编纂者的中文名字叫杂哈劳(1814年至1885年),是《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过程中的谈判翻译,也是俄驻华第一个领事(伊犁)。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过程中任俄“全权会勘地界大臣”,擢我西部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清(同治朝)《筹办夷务奏折》里上折的人骂他奸诈。 杂哈劳1840年随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北京,一住就是10年。他的身份是学员,有充分的机会研究满汉语。《满俄大辞典》于1875年出版,号称积20年之功,当不为虚词。1972年苏联满学界仍然觉得杂哈劳的辞典和满语语法著作是“不可替代的参考书”。 笔者淘得的《满俄大辞典》是1939年北京杨树岛印刷局照相影印的本子。读李雪涛著《日尔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外研社2008年6月),了解到杨树 岛印刷所恰是1939年由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洪涛生(1878年至1955年)创立的,地址在今北京城广安门外南河泡子27号。不才很有书缘,碰巧手里另有一册1939年北京杨树岛印刷局影印的袖珍本《欧皮支诗选》。扉页有创建北大德语系的杨丙辰先生手书“诗人欧皮支殁后三百年之纪念”,落款时间是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总有念头去东直门一窥“俄罗斯馆”(北馆),想看看杂哈劳当年学习满语的场所,想寻找“罗刹庙”的踪迹,想探访“胡家圈胡同”,甚至想去青年湖看俄国人在北京归土的所在。可惜啊,“北馆”是俄罗斯使馆的所在地,不得入。东直门附近现在只 有一个叫“胡家园”的地方,不知与300多年前安顿“雅克萨战役”罗刹战俘的那个“胡家圈”有没有关系。听说传教团1914年重建的藏书楼还在,那也只是听说而已。1900年前的“俄罗斯馆中外书房”更是遥远的想像了。不过,我相信杂哈劳编辞典的时候得益于此不少。 惟一的满语专家 即便从17l5年俄国东正教第一届传教团入北京算起,满语俄语互译互注的历史也近300年了。满语是清朝皇室使用的语言,满族人祖先居住地又是俄国与大清国通商必经之地.可想而知满语在俄国人眼里有多重要。据阎国栋先生的研究:“满学在俄国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建立。”(《俄国汉学史》)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定,俄国派学员随传教团来北京学习满汉语。学有所成者如罗索欣日后成为俄皇家科学院满汉语翻译。罗索欣翻译了舞格寿平的《满汉字清文启蒙》,将俄语语法书翻译成满文(《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曾是清廷俄文馆的教科书)。 俄国第一批满语词典是安·弗拉德金编写的。据说他未出版的满汉俄词典多达5部:利波夫措夫1838年出版《满语词典》;卡缅斯基的满学成就《汉蒙满俄拉丁词典》未出版;列昂季耶 夫斯基的《汉满拉丁俄语词典》依据的是《康熙字典》、《汉字西译》和《清文鉴》等工具书;俄国第一个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编有《满汉俄词典》;王西里被视为俄国“19世纪下半期最大的汉学家”,他编写的《满俄词典》包含满语的拼读发音方法;再往下数就是本文的对象杂哈劳的《满俄大辞典》了。 王西里称杂哈劳为俄罗斯“惟一的满语专家”并推荐他到圣彼得堡大学去任教。因为《满俄大辞典》,圣彼得堡大学免答辩给了他博士学位。皇家地理学会也因此书颁给他奖章。 肖玉秋教授著《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也是一部资料详实的书。该书第三章第三节涉及传教团的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中谈到杂哈劳时说道:“他在参考中俄两国以往满语辞书的同时,还阅读利用了大量已经失传的满文刊本与抄本。” 这正是杂哈劳辞典的价值所在了。收藏老字典、老辞典之所以有意义,正因为它们保留了许多失传本的内容。 1939年的巧合 1939年北京杨树岛印刷局影印杂哈劳1875年版《满俄大辞典》为16开、布面精装、1129页的巨册。书口三边蜡染。扉页和前言首页均套红。版权页有“中国印”三个中文字。“1939年8月影印150册”并“北京杨树岛印刷局”字样皆为英文。扉页前空白页有“满铁”三枚藏书印,分别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藏书之印”“满铁上海事务所图书印”和“上海满铁事务所”。 “满铁”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情报机构,与兼有搜集情报功能的俄国传教团出身的杂哈劳的辞典发生联系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情。我的盖有“满铁”印章的藏书另有英文版《白银的历史》,比较起来,《满俄大辞典》要“学术”得多。然而,一沾上“满铁”的字样,总让人想起“掠夺”之类的字样来。1939年的北京又是什么地方?我疑心这150本影印《满俄大辞典》是“满铁”下订单要的东西。《欧皮支诗选》里有一篇《敬告读者》,里面的宗旨是要中国人学习德国文化。这本巴掌大小的诗集就是杨树岛影印的第一本德国经典文本。 巧的是,与《满俄大辞典》杨树岛影印本有关的种种都发生在1939年。 另外巧合得十分有趣的是:杂哈劳通过满文译本研究过《西厢记》,并选取部分段落作课徒的教材;洪涛生则翻译过《牡丹亭》。 洪涛生也富有藏书,据说他是为了办杨树岛而搜集典籍的。李著说他的藏书为首都博物馆所的。这乃是题外话了。 我住处离广安门外很近,然而,还是不知道“南河泡子”的位置在哪里,无从凭吊遗迹。不过,“南河泡子”印的《满俄大辞典》我终究拥有一本,于愿足矣, 摘自《中国收藏》2011年第一期 106-108页 |